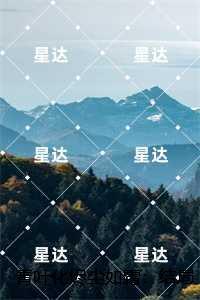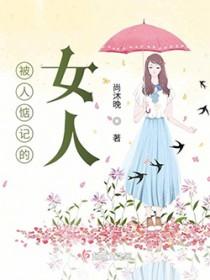大文学>末世毒妃:冷宫嫡女的逆袭之路 > 第256章 她不说话的时候连石头都学会了写诗(第2页)
第256章 她不说话的时候连石头都学会了写诗(第2页)
墨迹浮现时,墙面出轻微的“滋滋”声,如同雨水滴入热锅,又似血肉愈合。
字迹漆黑亮,散出淡淡的铁锈味——那是血与墨交融的气息。
“寒衣普赐,老弱优先。”
更诡异的是,那些字迹每成型一字,便有一缕极淡的红雾从地底的砖缝中丝丝缕缕地升腾而起,在空中凝成一个短暂的、模糊的人形轮廓,随即消散。
红雾掠过鼻尖时,带来一丝温热与腐甜交织的气味,令人胸口闷。
轮廓虽无形貌,却让人心头骤然一紧,仿佛被无数双眼睛静静注视。
蓝护卫的瞳孔骤然收缩,他认得那轮廓——那是数十年前,在这座织坊里因酷吏盘剥、冻饿而死的数百名女工的怨魂!
她们没有嘶吼,没有索命,只是在阿阮的引导下,静静地“看”着那迟到了数十年的公道,被一笔一划地写在她们倒下的地方。
那一刻,风停了,连远处犬吠也消失了。
天地间只剩那喑哑之声,与墙上字迹生长的细微响动。
蓝护卫没有惊扰这神圣而悲怆的一幕。
他悄然退走,回到井卫司,在呈给苏烬宁的密报末尾,只用最简洁的语言写道:“西坊碑林夜有吟声,似亡者也在学写字。”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笔尖落下时,墨迹微微洇开,像是一滴未落尽的眼泪。
翌日,苏烬宁换上一身灰扑扑的粗布衣,扮作一个拾荒的老妪,在人声鼎沸的北市一角静坐了整整一日。
市集喧嚣,叫卖声、讨价声、孩童嬉闹声混成一片,但她耳中却仿佛隔了一层水幕,只听得见愿匣开启时纸条滑落的沙沙声。
她看到,越来越多的百姓不再仅仅是被动地等待政令颁布。
他们将自己的诉求、邻里的纠纷、对未来的期盼,写在小小的纸条上,郑重地投入民策台边新设的“愿匣”。
纸张摩擦箱壁的声音清脆而庄重,如同献祭。
次日清晨,匣中的纸张尽数消失,而民策台的墙壁上,却多出了对应的回应条文。
那字体驳杂不一,有的娟秀如春蚕吐丝,有的粗犷似刀劈斧凿,仿佛出自百家之手,内容却逻辑贯通,情理兼备。
更有甚者,两名素不相识的老者为了一条田间灌溉分水令争执不下,各自写下方案贴于墙头,一夜过后,两张纸条竟自行融合成了一份详尽周全的折中之策,落款处一片空白。
苏烬宁蹲在墙角,伸出枯枝般的手指,用一截捡来的炭条,轻轻描摹着那行融合后字迹的起笔走势。
炭粉沾在指腹,粗糙而温热,仿佛触摸到了万民心念流动的脉搏。
她低声自语,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:“不是我在听他们,是他们开始……彼此听见了。”
这句话落进风里,轻若尘埃,却在她心中掀起惊涛骇浪。
这份认知,远比凤印显灵更让她感到震撼。
深夜,林墨终于在药王谷最深处的秘藏《灵识通纪》中,找到了关于“司名者”的真正记载,那段文字被尘封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,仿佛刻意不想被人现。
羊皮卷轴展开时出干涩的“咔咔”声,边缘碎裂,扬起细小的尘埃,呛得她咳嗽不止。
但当目光触及那行字时,她全身如遭雷击,指尖剧烈颤抖,几乎握不住卷轴。
“司名者,其声不在喉舌,在万民共感之时;其权不在玺印,在众心自愿承继之刻。”
权力不是授予,而是承继!
林墨如遭雷击,她抓起那卷古老的兽皮,连夜策马奔向城外皇陵,不顾一切地求见已闭门谢客三月的紫大臣。
马蹄踏碎夜露,溅起冰冷泥浆,打湿了她的裙摆。
风灌进喉咙,带着荒野的枯草气息。
守陵的老人被惊动,他看着眼前失魂落魄的济世阁使,眼神枯寂。
当他那双枯槁的手颤抖着接过残卷,读到那行字时,整个人僵住了。
下一刻,这位见惯了朝堂风雨的老人,忽然老泪纵横,出了压抑多年的、野兽般的呜咽。
那声音低沉嘶哑,如同困兽哀鸣,在寂静陵园中久久回荡。
“先帝焚书坑儒那一夜……我……我亲手烧了那本《百姓名录》……整整三大箱,烧了三天三夜……”他浑身颤抖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火光冲天的夜晚,“我以为我烧掉了他们的根……可原来,原来名字是烧不死的!它们藏进了地下水脉,藏进了砖缝青苔,藏进了孩子们的梦话里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