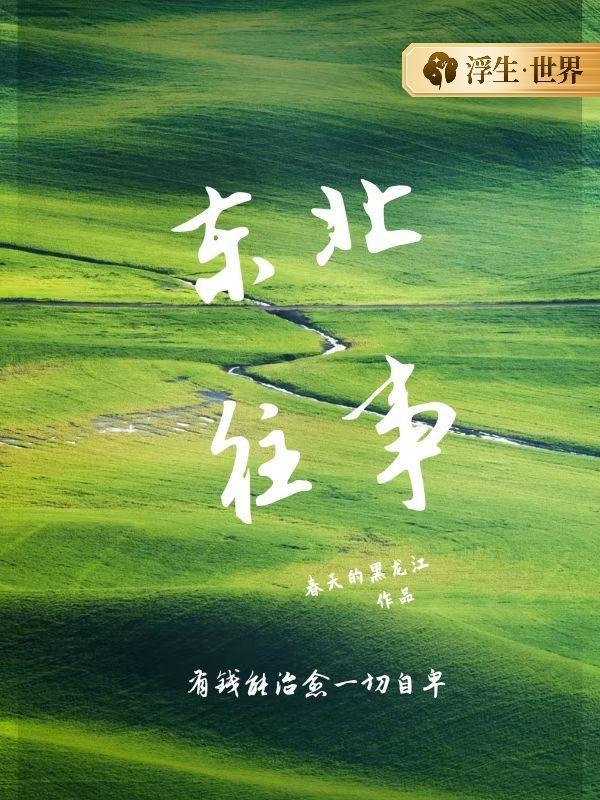大文学>等一场京雨 > 2530(第2页)
2530(第2页)
况且她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坚定。
“怎么一个人出来了?”身后传来赵赟庭低沉含笑的声音。
江渔深吸一口气,平复了一下心情才回头。
他在逆光里走向她,单手入兜,意态闲适,连短短几步路都这么潇洒。
其实江渔有时候挺佩服他,哪怕风雨飘摇,不知道未来如何取舍,他在她面前总这么镇定,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。
也给她一种一切都风平浪静的错觉。
江渔多看了他会儿,弄得赵赟庭都有些不自在了:“你这么看着我干嘛?”
他自己先笑了一下,想缓和一下两人间莫名紧张古怪的气氛。
虽然不明所以,但他能很敏锐地感受到她的不高兴。
江渔抿了下唇,若无其事地说:“没事,只是不太喜欢那样的氛围。你们聊的那些,我都不懂。”
“你不也读金融吗?”
“镀镀金而已啦,我们那是什么学校?”无非是多给自己留条后路,要是以后在圈里得罪了人混不下去了,还能有个文凭傍身。
若要说她学习有多好,那是无稽之谈。
她本来也不是多爱学习的人。
自由散漫惯了,她在学习上能投入的精力也很有限。而且过早地进入社会,接触了太多,被各种浮华功利所浸淫,这个时候再去投入学习,有些为时过晚。
“倒是我好心办坏事了,以后不叫那么多人来给你庆生。”
“别这么说。”
她这样不冷不热的,赵赟庭也觉得没意思。
好好一场生日会,这样不欢而散。
他后来接到个电话,撇下她去窗边听了会儿,回头自己先走了,只留下司机送她。
江渔望着他的背影,不奇怪他的拂袖而去。
再好的修养,也受不了这样的漠视,何况他本就是眼高于顶的人。
他连他父母的账都不买,何况是她的。
那晚,夜半时她醒了,出来上洗手间,却发现他还在书房。
书房的门半掩着,里面透出淡淡黄光,隐约有交谈声从里面传出。
安静中,还挺清晰。
“……调去南京有什么不好,你非要留京?风雨飘摇的当口,躲一时风平浪静,这个道理你不懂吗?不是不调你回来。在乎这一天两天的?你不是这么不能忍耐的人,究竟是为什么?”
“江永昌快倒台了,趁早和江家划清界限。你在犹豫什么……”
“赵赟庭,说话!哑巴了!”声音加重,平淡中透着威仪,是他母亲王瑄。
“没话说。”他不咸不淡地回敬。
那边约莫是骂了一声,将电话掐了。
他十指交握,略拄着下颌低头沉思,窗外树影摇曳,有一大片扑簌簌的阴影在他桌台前晃动,像蒙上一层阴翳。
江渔的脚步停在那边,没有去叩门,亦或者是不敢。
那一刻她似乎能感同深身他的纠结。
但是——她似乎也能预料到他后面的选择。
所以,让自己无情一点,是不是以后分别时会好受一点?
其实她确实是不理解他们这类人的,一开始阶层差距就很大。
就像她不能理解他母亲在她面前时谈笑风生、对她关怀备至,私底下却希望他们早点离婚。
就算是演戏,扪心自问,江渔都做不到。
可他们这类人,情感淡漠,似乎已经将面具自然地戴在脸上。
江渔压住心里的酸涩,老半晌没有动。
离开时,是黄俊毅送的她,表情还挺尴尬的。
为了避免他尴尬,江渔善解人意地笑了笑:“你不用为难,司机送我就好。”
“算了,还是我送你吧。赵四生气归生气,要是我真把你撇下,你看他回头怎么找我算账?!你要出了事,他第一个饶不了我。”
可能他本身也是热心肠的人,一路护送她回去。
赵赟庭的这些发小里,她也就跟黄俊毅相处起来并无障碍。
旁的人,哪怕温文客气,也始终带着高高在上的睥睨感,让人无所适从。
汽车在公路上安静行驶,窗外是急速掠过的树干和路灯的影子。
单调而乏味,和这京城郊外萧条的东景相得益彰。
江渔呼吸一口气,鼻腔里也像**涩的什么填满,呼吸困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