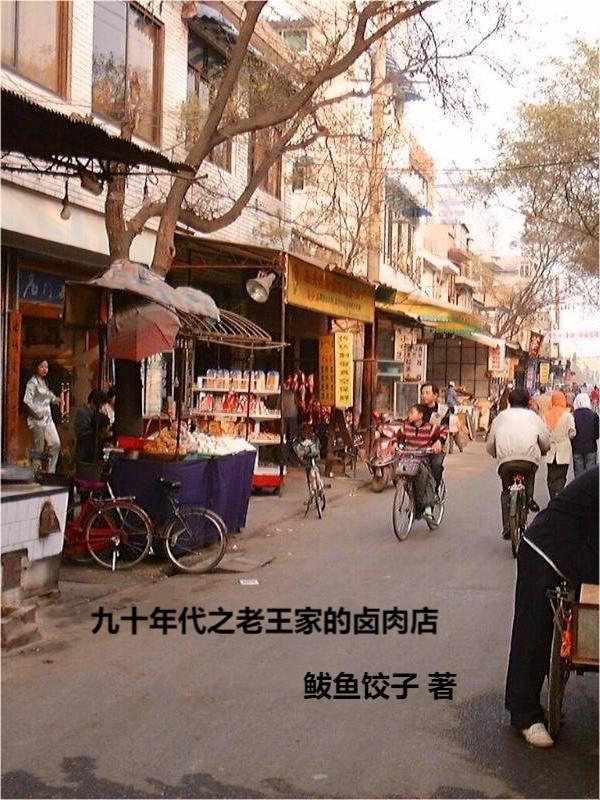大文学>每日沉沦资讯CP > 第207章(第1页)
第207章(第1页)
青年长舒了一口气,立马缩回了脚,脖颈却被人伸手勾住下压,上半身随之带低,同地上的挽明月吻到了一块。
不知在腥气里被强吻了多久,一被放开,青年就抓来衣服蹭掉脚上的白,又跑到外头好一番地洗脚。
再回来,见挽明月又躺回床上睡觉去了,他由于常年防刺客久,习惯了不开窗,使得屋里腥味都散不干净。
青年穿齐整衣裳,替他打开屋里的窗户散气。因为早先那件事,道别都没敢到他床边,只站在门口问他需不需要自己替他去跟药铺的老板请假。
“明个儿我随便编个理由就行了。”
“那你要不要吃饭?”
“不吃,睡觉。成日天不亮就去堵你,当我是铁打的吗?你还非要闹。”
青年觉得再说下去,自己一定又成没理的那个,扭头出门买了份饭,回来搁到挽明月屋里。
屋里通了阵风,味道散净了,挽明月还在休息,青年担心他受凉,临走前又把窗户关上。
如此相安无事到次日,然而临到晚上,青年在楼下招待客人,远远就见一高大的人进到茶楼来。
夜里挽明月照常又把青年骗到家里,青年进到房里,一眼就见到了床底下铺的虎皮毯,浑身哆嗦了一下。
挽明月反手插上屋门。
这回是浓在了脚背上,温温的黏稠顺着脚背缓缓下流。青年浑身不适,气得直接伸脚往挽明月身上蹭。
挽明月面上还蒙着一层浅淡的绯色,像被火烤过的汉白玉。他不同青年计较,放着怀给他擦,任他把身上蹭满,还要从他脚上挑起一缕自己的白,喂到青年嘴边去。
青年震惊地躲开,大声道:“这东西刚才在我脚上!”
因为此前的经历,青年对这事多少有些神经质,总觉得还不干净,一双脚在挽明月身上到处乱蹭。
挽明月担心再给他撩出火,伸手握住他的脚掌,开口就是瞎话:“哦,从前逼着让你吐出来,你都非得吃下去。”
话音没落,青年提起另一只脚,飞速往挽明月左胸踹了一脚。
他恼急了,劲道大,这一脚甚至于有些泛痛。可他一用狠,挽明月就来兴致,起了捉弄他的心思,一言不发蓦地朝他栽倒过去,把他摔在床上。
青年知道自己没轻没重惯了,顿时着了急,扒开他胸口去看伤势。
“心伤从外头瞧不出的。”挽明月故作虚弱道:“只有叫明月哥哥才能止痛。”
青年不胜其烦,近些时候给人打趣惯了,也破罐子破摔,皱着眉连声敷衍:“明月哥哥!明月哥哥!明月哥哥!”
挽明月给他敷衍笑了,见不到他气得发火,简直失去一个趣儿,叹了一声,翻身躺倒在床上。
半天,青年都坐到床边穿鞋准备离开,他又新想了个解闷的乐子,从后头抱住青年的腰,嘴唇亲吻着青年的侧脸,扮出可怜的语气:“今晚留下来好不好。”
青年警惕地歪头看他一眼,穿鞋套袜的动作顿时加快了。
挽明月紧抱他的腰,制止他离开,向他灌输:“你以前还想叫我相公,不过我觉得太过了,没让你叫,现在真是怀念。你叫我声相公,我就让你走,好不好呀?”
韩临忍不住:“挽明月你究竟要不要脸!”
三个残疾人
挽明月挑眉:“哦,你不装啦?”
韩临当即起身要走,给身后的人搂住腰又拽回去。
只听他背后的男人语气失望道:“你不装,我还怎么占你便宜?”
韩临推他一把,为他明目张胆的无耻咬牙切齿:“你能不能要点脸!”
男人将脸埋到他颈窝里,笑着说:“我不要脸,我要你。”
韩临一时给他堵得没话说。
上官阙穿着女人衣服吓韩临那天,韩临跳到湖里,湖水冰凉,等满心的恐惧冷静下来,他意识到,他跟上官阙缠得太紧了,再这样下去,等待他的只有上官阙漫无止境的不安与试探。他无路可逃之际,想到了死亡,死亡才是真正的快刀斩乱麻。
自杀是很好的,一了百了。可对于韩临来说,他从小就是从闷死人的黄土里使了劲钻出来的。就像乞讨过的人珍惜粮食,韩临历经饥荒,丧失双亲,流浪,一步步艰难地活下来,由而更珍惜性命,死亡在他固有的理念里从来不是轻松的,他更不舍得自杀。所以韩临想到了借助别人来死。
他磨薄刀,用柔情哄骗上官阙,对挽明月极尽冷漠。
可是他实在太想活着,追杀过程中身上带了重伤,心知再强追一定会死,目的一定会达成,可面前是所有凡人都畏惧的死亡,他难免不坚定,连摸刀都手抖。凡事凡物在这时候都显得很美好,吸引着他驻足,都足以挽留住他活在这个世界。
韩临犹豫过很多次,第一次姑娘提醒他状态很差,他看看影子,觉得自己这样满心疲惫活着只会更累,所以他选择了死亡。第二次他视作女儿的红袖过来,带着曾经上官阙违命救他的令牌,鲜少流泪的姑娘哭了,又让他心软。第三次见到了花剪夏的丈夫,他和韩临聊天,却不杀韩临,只指出你很可怜。韩临害怕死亡,却更不敢想自己回去,还要造成多少花剪夏这样的悲剧。往后的追灯令再找上门来,韩临一样都不肯接,坚持赴死。
韩临想过自己的所作所为,挽明月一定会难过,可要是把真实意图告诉挽明月,挽明月一定不会帮他。但韩临了解他,对于自己的追杀,相比难过,挽明月更生气。然而就算挽明月再生气,自己死了,他多少能有点解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