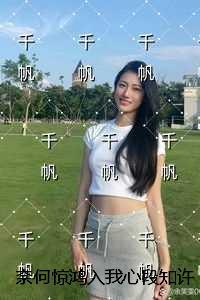大文学>北洋醉城隍 > 第374章 裂痕初现暗流汹涌(第1页)
第374章 裂痕初现暗流汹涌(第1页)
议事厅的檀香烧到第七柱时,陆醉川的靴底碾过青石板,带起一阵风将烛火吹得摇晃。
他怀里的地图被体温焐得烫,隔着粗布衣襟都能触到那些凸起的纹路——那是用城隍血印烙下的魂渊之眼坐标。
"都到齐了。"沈墨寒站在长桌尽头,指尖轻点桌面。
她素白的袖口垂落,露出腕间银铃,此刻却未出半分声响。
陆醉川将地图平铺在檀木桌上。
牛油灯的光顺着纸纹流淌,映出"魂渊之眼"四个暗红血字,像滴在宣纸上的血珠,正缓缓晕开。"这是从神格祭坛拓印的。"他喉结动了动,指腹压在血字上,"传说中封印邪神本源的核心,就在这里。"
"最后的机会?"李啸天的声音像破风的刀。
这位激进派领猛地拍案,茶盏被震得跳起来,琥珀色的茶汤溅在地图边缘,"还等什么?
等邪神把爪牙伸到咱们脖子上?"他腰间的玄铁剑嗡鸣,剑穗上的红绒被气浪掀得翻飞。
清风道长的手指在典籍上顿住。
他穿了件洗得白的道袍,袖口还沾着星尘——今早他刚在观星台推演过星轨。"李堂主莫急。"他翻开一页泛黄的《幽冥禁录》,指腹划过一行朱砂批注,"二十年前,我师兄弟三人试图硬闯魂渊,结果被三重血煞阵绞碎了两具法身。"他抬眼时,眼角的皱纹里凝着霜,"那些禁制不是靠血气能破的。"
厅内温度骤降。
支持李啸天的青衫客们握紧了腰间的符袋,几个年轻弟子的指节捏得白;倾向清风道长的老修士则垂眸抚须,有人悄悄将茶盏往自己跟前挪了挪——这是他们商量对策时的暗号。
"报——!"
木门被撞开的声响惊得烛火炸出灯花。
一个十五六岁的杂役弟子跌跌撞撞冲进来,额角挂着汗,道袍前襟沾着泥:"外、外围防线!
方才巡查时,西哨的镇魂铃突然全碎了!
守夜的张叔说说闻到腐肉味,像像当年邪神祸乱时的阴煞气!"
李啸天突然笑了。
他的笑声震得梁上积灰簌簌落下,玄铁剑"噌"地出鞘三寸,寒光扫过众人:"听见没?
敌人已经动了!
等你们破完禁制,魂渊之眼早被邪神夺回去了!"他转身看向身后的支持者,剑穗上的红绒在风里猎猎作响,"今夜子时,我带暴雷营出。
想杀邪神的,跟我走!"
"李堂主!"清风道长霍然起身,道袍下摆扫落了半卷《幽冥禁录》。
他的右手按在桌沿,指节因用力而泛白,"你可知孤军深入是什么下场?
当年镇北军就是这样被阴兵围歼的——"
"够了!"
陆醉川的声音像块淬了冰的铁。
他站在长桌位,断刀不知何时已出鞘三寸,刀身映出他绷紧的下颌线。
方才还在争执的众人突然噤声——他们想起三个月前,这个曾在酒楼跑堂的醉汉,就是用这把断刀劈开了九幽冥关的鬼门。
沈墨寒的指尖在袖中掐了个"观命诀"。
她垂眸望着那个报信的杂役弟子,眼底泛起一层淡青色的雾气——阴阳窥命术下,少年的经脉里盘着条细如丝的黑蛇,蛇头正对着心脏。"傀儡蛊。"她的声音轻得像片落在陆醉川肩头上的雪,"邪神余党的手段,专门用来煽动人心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