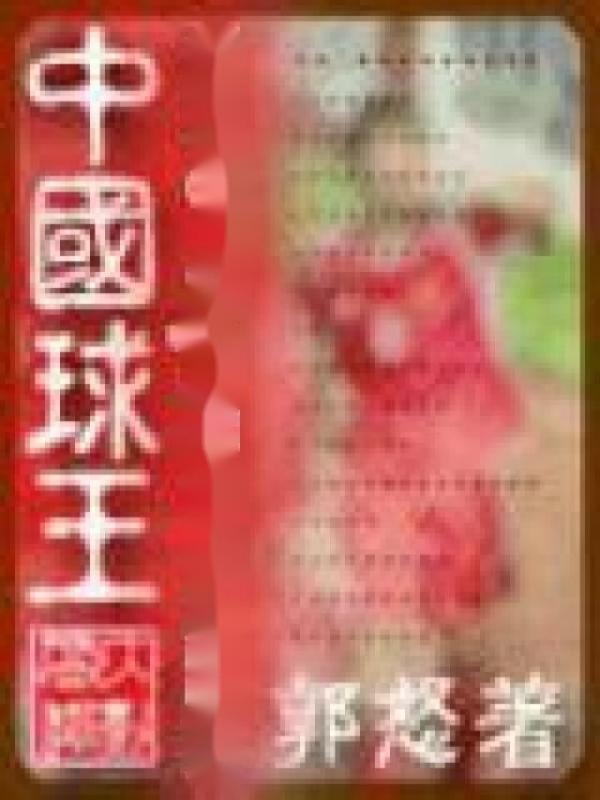大文学>影视:潇洒的人生从欢乐颂开始 > 第218章 晨曦微澜古镇闲行与禅茶一味(第2页)
第218章 晨曦微澜古镇闲行与禅茶一味(第2页)
小主,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,后面更精彩!
她顿了顿,声音低了下去:“直到……我最好的朋友离开。我才现,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陀螺,不停地转,却忘了为什么而转。所以,我辞职了,来了这里。”
她没有提陈南星的名字,但那份深刻的失去和随之而来的巨大空洞,在场的人都隐约感受到了。大麦和娜娜都露出了理解和同情的眼神。
王也一直安静地听着,这时才放下碗,拿起旁边的水杯喝了一口,语气随意地接道:“都不容易。我以前……嗯,算是创业吧,搞了个小公司,做短视频相关的。”
他斟酌着用词,没有透露“抖手”的存在。“最开始的时候,最难了。没钱,没人,没方向。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地找投资,见人就得装孙子,陪笑脸。通宵是家常便饭,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团队里人心惶惶,今天这个要走,明天那个要撤。最煎熬的还不是身体上的累,是那种看不到希望、每天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在痴人说梦的绝望感。感觉前面是黑的,不知道路在哪儿,还得硬着头皮带着剩下的人往前走。那滋味,确实不好受。”
他说得很平淡,甚至带着点自嘲的笑意,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。但许红豆、大麦、娜娜都能想象出那份“煎熬”的重量。那是一种属于创业者特有的、在绝望中寻找希望、在黑暗中开辟道路的孤独与挣扎。
“后来呢?”娜娜轻声问。
“后来啊,”王也笑了笑,那笑容里有种云淡风轻的释然,“运气好吧,熬过来了,找到了一点方向,慢慢就顺了。不过那种天天悬着心的日子,是真不想再经历第二遍了。”
他没有细说“顺了”之后是怎样的光景,但那份举重若轻的态度,反而更让人感受到他背后可能经历的波澜壮阔。
一顿简单的早餐,因为这几段坦诚的分享,而多了几分温度。每个人都曾在自己的人生战场上奋力拼杀,带着或深或浅的伤痕,最终在这里,在这个偏远的白族小院,短暂地交汇,分享着彼此的疲惫与疗愈。
吃完早餐,许红豆想起手机虽然修好了,但还没去镇上取,而且身上现金也不多了。她正想着怎么开口,王也像是看穿了她的心思,晃了晃手里的车钥匙(还是谢之遥那辆皮卡的):“我要去趟镇上办点事,顺便取个快递。你要不要去把手机拿了,再取点钱?古镇那边银行和手机维修点挨着。”
“好,谢谢。”许红豆正需要这个台阶。
两人跟大麦、娜娜打了声招呼,便开车出了。车子驶出云庙村,朝着最近的一个古镇开去。一路上依旧是湖光山色,美不胜收。王也车开得很稳,放着轻松的音乐。许红豆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,想着早餐时大家的分享,心里的郁结似乎又散去了一些。
到了古镇,王也去快递点取东西,许红豆则先去银行取了现金,然后去手机维修店取了修好的手机。开机,检查,功能基本都恢复了,只是外壳上还留着一点难以完全消除的磕碰痕迹,像是这段旅程开端的一个小小印记。
取完手机,看时间还早,两人便在古镇里随意逛了逛。古镇不大,但很有味道,青石板路,白墙黛瓦,小桥流水,沿街开着各种售卖扎染、银器、茶叶、鲜花饼等特产的小店。许红豆想着给家里和姐姐寄点特产,便挑了几样,写了地址让店家直接打包邮寄。
从特产店出来,许红豆现自己手腕上的手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。她皱了皱眉,下意识想用手机看时间,又想起手机刚修好,电量不多。正想着要不要找个地方给手表上弦或者对时,就看到街边有几个小孩在跳房子,其中一个稍大点的男孩手腕上戴着一只显眼的、带有夜光数字的电子表。
许红豆灵机一动,从刚买的零食袋里拿出一包当地特色的梅子干,走到那几个小孩面前,蹲下身,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:“小朋友,姐姐的手表坏了,能不能借你的手表看一下现在几点了呀?姐姐用这个好吃的梅子干跟你换,好不好?”
那男孩看看她手里的梅子干,又看看自己手腕上那块对他来说很“酷”的电子表,犹豫了一下,点了点头,很爽快地把手表摘下来递给她:“给,姐姐。现在是十点三十七分。”
“谢谢!”许红豆接过手表,看了时间,然后把梅子干递给男孩,又拿出一张便签纸和笔,写了一张“欠条”:“今借到xxx小朋友手表一看,用梅子干一包交换。如需归还,可凭此条到云庙村有风小院找许红豆姐姐。谢谢!”她写得很认真,还画了个笑脸。
男孩接过“欠条”,似懂非懂,但觉得很有意思,咧开嘴笑了,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牙床。其他小孩也好奇地围过来看。
王也站在不远处,看着许红豆蹲在那里,用一包梅子干和一张童趣的“欠条”跟小孩换手表看时间,脸上不禁露出笑意。这个女人,有时候冷静理性得像个精密仪器,有时候却又会流露出这样孩子气、充满生活智慧的一面。很有趣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对好时间,把手表(和欠条)还给男孩,又分了些零食给其他小孩,在孩子们“谢谢姐姐”的欢快声音中,许红豆站起身,拍了拍手,心情莫名地好了起来。这种简单直接的、充满童真的互动,让她暂时忘记了那些沉重的事情。
“解决了?”王也走过来,笑着问。
“嗯,解决了。”许红豆点点头,扬了扬手里剩下的零食,“还多了点‘战利品’。走吧,该回去了。”
下午回到“有风小院”,院子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茶香。马爷居然没在打坐,而是坐在桂花树下的石桌旁,面前摆着一套古朴的茶具,一个小泥炉上的水正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。
看到王也和许红豆回来,马爷抬起眼皮,对他们招了招手,声音平和无波:“回来了?过来,喝杯茶。”
两人走过去,在马爷对面坐下。马爷动作舒缓地烫杯、置茶、冲泡、出汤,手法娴熟,带着一种独特的韵律感。他将两杯澄澈金黄、香气清雅的茶汤分别放到王也和许红豆面前。
“尝尝,今年的春茶,自己晒的。”马爷说道。
王也端起茶杯,先闻了闻香,然后小啜一口,在口中略作停留,缓缓咽下,点了点头:“香气清幽,回甘不错,是好茶。马爷好手艺。”
许红豆也学着样子,喝了一口,她不懂茶,只觉得入口微苦,随即转为清甜,一股暖意顺着喉咙下去,很舒服。
“茶如人生,先苦后甜。”马爷自己也端起一杯,慢慢品着,目光有些悠远,“静心品之,方能得其真味。你们年轻人,心都太浮,被外物所扰,难得清净。试试打坐,静心凝神,或许能看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”
他又开始讲他那套“心静自然凉”的哲学了。许红豆听得半懂不懂,但觉得在这样宁静的午后,听着这些玄妙的话,喝着清香的茶,倒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。
王也却笑了笑,放下茶杯,看着马爷,语气平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犀利:“马爷,您这打坐的法子,讲究的是形神俱寂,物我两忘。想法是好的,但方法上,依我看,有点过于执着于‘形’了。”
马爷撩起眼皮,看了王也一眼,没说话,但那眼神里透出询问。
王也继续道:“您看您,每次打坐,姿势一定要标准,环境一定要安静,心里默念着要静、要空。这本身,不就是一种‘执’吗?心里想着‘我要静’,这念头一起,心就已经不静了。真正的静,不是靠强求的姿势和环境得来的,是心里放下了,自然而然就静了。您这电话一响,”他指了指马爷放在石桌角落、调了静音但屏幕偶尔会亮起的手机,“您这眉头是不是下意识就动了一下?心里是不是闪过一丝‘烦’?这说明,您心里还在‘听’,还在‘分别’,离真正的‘静’,还差着点意思。”
他这番话,说得不紧不慢,却直指核心。许红豆有些惊讶地看着王也,没想到他还懂这些?听起来还挺有道理。
马爷沉默了片刻,脸上那副高深莫测的表情第一次出现了一丝裂痕,他深深地看了王也一眼:“没想到,王施主对禅理也有研究?”
王也摆摆手,笑道:“研究谈不上。就是高中毕业那年暑假,闲着没事,跑去武当山住了一阵子,跟着观里的道长学了几天粗浅的吐纳和静坐。道长说,道法自然,静心不是把心变成一潭死水,而是像这院子里的风,该来的时候来,该走的时候走,不迎不拒,不住不留。你越想着怎么抓住风,风越从你指缝溜走。不如就坐在这儿,感受风,也感受自己,风是风,你是你,两不相碍,也就清净了。”
他这番比喻,比马爷那套玄之又玄的说法,更通俗,也更贴近许红豆的理解。她若有所思。
马爷没再说话,只是拿起茶杯,又喝了一口,目光重新变得平静悠远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就在这时,他放在石桌上的手机屏幕又亮了起来,这次是来电震动。马爷瞥了一眼,手指在屏幕上轻轻一划,挂断了。动作自然流畅,之前那微不可察的皱眉,这次似乎真的没有了。
王也笑了笑,没再继续这个话题。
三人静静地喝着茶,享受着午后慵懒的时光。茶香、花香、微风,还有那份难得的、无需多言的宁静。
就在这时,王也的手机响了。他拿起来一看,是个陌生的本地号码。他挑了挑眉,接通。
“喂,你好。”
“请问是王也先生吗?”电话那头是个中年女声,带着焦急和试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