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文学>成语认知词典:解锁人生底层算法 > 第673章 打理家宅(第1页)
第673章 打理家宅(第1页)
那封送往江南道的信,如同石沉大海。
没有回音,没有反应,甚至没有一丝涟漪通过官方的渠道传回。谢云归仿佛真的彻底遵循了信中的“旨意”——以公务为重,循例呈报有司,不再专呈于她。
公主府的日子,以一种近乎凝固的平稳,继续向前流淌。
沈青崖似乎也真的将那场疾驰驿站的怒火,与那封决绝的信,一同封存了起来。她不再提起江南,不再过问任何与谢云归相关的细务,甚至当巽风按例呈报江南道官员动态时,听到那个名字,她的眼神也不会有丝毫波动,只是淡淡颔,示意继续下一项。
她将全部的精力,投注在了两件事上:朝中必要的事务,以及,打理公主府这座华美而空旷的“家宅”。
打理家宅,成了她生活中一种新的、带着明确秩序感的仪式。
每日清晨用过早膳,送走前往书房的顾晏清后,她便会移步至府中东南角的“账房”。这里原本只是存放府中日常用度册籍的寻常屋子,如今被她收拾出来,临窗设了一张宽大的紫檀木书案,上面整齐摆放着算盘、笔墨、各色标签,以及一摞摞装订好的册子。
她开始亲自核对公主府历年来的收支账目。田庄的租子,铺面的红利,宫中按例放的俸银与赏赐,府中上下百余口人的月例开支,四季衣裳的采买,器具的维护,宴客的用度……一桩桩,一件件,浩如烟海,琐碎至极。
管事嬷嬷起初战战兢兢,捧着厚厚的账册,小心翼翼地回话,生怕哪里出了纰漏,惹得这位心思深沉、近日气压极低的主子不快。但沈青崖只是平静地听着,偶尔问上几句,指尖划过纸面上密密麻麻的数字,眼神专注而清冷,并无苛责之意。她甚至能指出某年某月某笔采买中木材单价略高于市价的疑点,或是某处田庄收成与往年相比不合理的微末差异。
她的记性好得惊人,心算极快,对银钱数目和物资市价似乎有着一种天生的敏锐。不过旬日,几位管事的嬷嬷和内外院的掌事,在她面前回话时,便再不敢有丝毫轻忽与隐瞒,毕恭毕敬之余,也隐隐生出几分真正的敬畏——这位深居简出的长公主,并非不食人间烟火,她只是将那份掌控局面的能力,从朝堂延伸到了这府邸的每一个角落。
核对账目之外,她开始重新梳理府中人事。
哪些老仆到了该荣养的年纪,哪些年轻的下人可堪栽培,哪个位置的职责可以合并以节省冗费,哪里的规矩需要重申或调整……她并不大刀阔斧地变动,而是像修剪一株过分蔓生的花木,耐心地、一点点地,剔除枯枝,扶正歪斜,让整座府邸的运作变得更加高效、清晰,也更符合她“清净”的意愿。
她甚至亲自过问了后园暖房的花草。哪株兰花该分盆了,哪片牡丹需要追什么肥,今年夏日引种的几株睡莲是否适应了京中的水土……花匠是个老实巴交的中年人,起初见到公主亲临,吓得话都说不利索。但沈青崖并不介意,只静静听着他结结巴巴的禀报,偶尔问一句专业的问题,目光掠过那些生机勃勃或娇嫩欲滴的植物时,眼底会浮现一丝极淡的、近乎虚无的柔和。
她也会在天气晴好的下午,召府中供养的那位老琴师到水榭弹琴。不要那些热闹的曲调,只要最清寂的古曲。《幽兰》、《流水》、《梅花三弄》……琴音泠泠,穿过水面的微风,散入庭院的绿荫深处。她往往只是独自坐在水榭中,面前摆着一杯清茶,并不认真去听,眼神空茫地望着某一处水面或枝叶的颤动,仿佛那琴声只是她放空思绪时一道合适的背景音。
顾晏清的存在,在这座逐渐被沈青崖亲手梳理得井井有条的府邸里,愈像一个安静的影子。他依旧每日准时出现在早膳桌上,沉默地用饭,然后消失在那间几乎成为他全部天地的书房。沈青崖处理家务时,他从不会来打扰。偶尔在庭院中相遇,他也只是停下脚步,垂躬身,唤一声“殿下”,待她微微颔走过,便继续自己的路。
他们像两条平行线,各自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,永不相交,却也互不干扰。这或许,正是这桩婚姻最“成功”的地方。
这一日,沈青崖正在账房核对今年夏季采买冰块的预算。京城暑热,贵族之家多用冰窖储冰消夏,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她正凝神比较几家皇商往年的报价与口碑,茯苓悄步进来,低声道:“殿下,安国公夫人递了帖子,说明日想来府中拜会,说是……得了些上好的血燕,想献给殿下滋补身子。”
安国公夫人。沈青崖执笔的手微微一顿。
安国公世子那场荒唐的闹剧之后,安国公府一直战战兢兢,闭门谢客,生怕被迁怒。如今忽然递帖拜访,还用了“献礼”这样的字眼,无非是试探,是讨好,是想看看这位长公主是否还记着前仇,也或许……是想重新建立起某种联系。
沈青崖沉默片刻,将笔搁下。
小主,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,后面更精彩!
“回了罢。”她声音平淡,“就说本宫近日潜心礼佛,需静心休养,不便见客。国公夫人的心意,本宫心领了。”
“是。”茯苓应下,却并未立刻离开,脸上露出一丝犹豫。
“还有事?”沈青崖抬眼。
“是……关于顾驸马。”茯苓声音压得更低,“今日早间,驸马爷身边的小厮无意中说起,驸马爷昨夜在书房,似乎……咳血了。虽然驸马爷立刻遮掩了过去,也不许声张,但那小厮心中害怕,偷偷告诉了奴婢。”
咳血?
沈青崖眉梢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。顾晏清身子骨弱,她是知道的。大婚那日他脸色便不好,这些时日更是深居简出,气色一直未见红润。只是她从未过问,他也从不提起。
她靠在椅背上,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光滑的紫檀木桌面。暖黄的夕阳从西窗斜射进来,落在她半张脸上,另一半隐在阴影里,神色莫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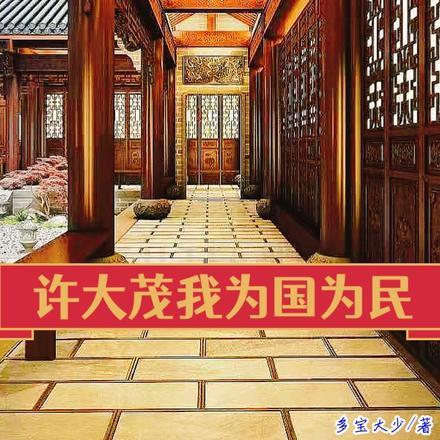
![我们这里禁止单身[星际]](/img/48107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