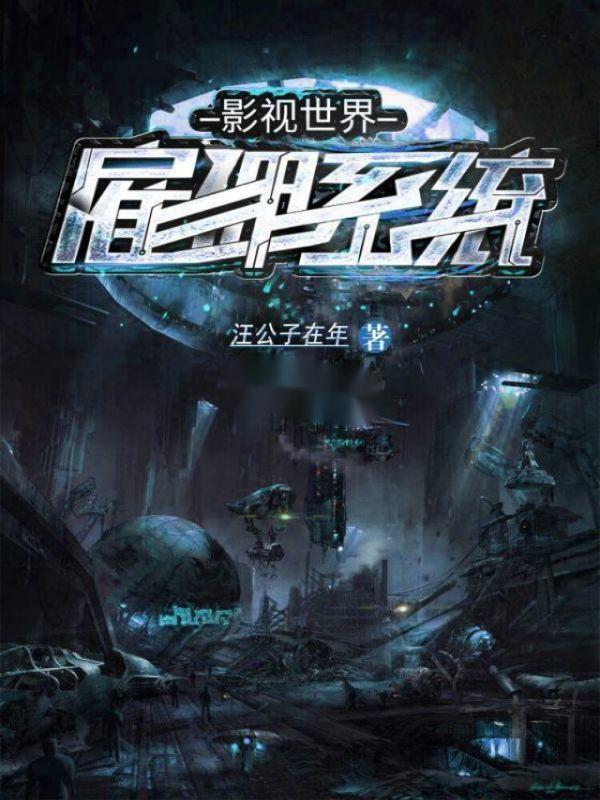大文学>凰倾天下:从罪奴到女帝 > 第202章 烽烟起南北峙(第1页)
第202章 烽烟起南北峙(第1页)
沈璃起兵的消息,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,激起的涟漪以惊人的度扩散至帝国的每一个角落。
精锐铁骑三万,步卒两万,这是沈璃经营多年的嫡系部队。这些士卒大多是在苦寒之地与蛮族作战中磨砺出来的百战之师。铁骑的战马皆选自北地特有的寒原马种,体型虽不如中原战马高大,却耐力惊人,能在积雪中连续奔袭三日而不衰。他们的铠甲采用北地特有的冷锻技法打造,在晨光中泛着青灰色的寒光,仿佛裹挟着北疆风雪而来。
更令人不安的是,这支军队的装备之精良远朝廷预料。探子回报,沈璃军中竟有大量原本只应配备给中央禁军的制式军械——精钢打造的横刀、射程达两百步的硬弩、甚至还有三十余架用于攻城的投石车。这些装备的来源成为帝国朝堂上激烈争论的谜题,有人怀疑是兵部有人私通,有人猜测是沈璃通过边贸从西域诸国购得,更有人惊恐地推测:北疆的军工作坊,恐怕早已在暗中达到了惊人的规模。
消息传出的第七日,第一个响应的藩镇出现了。镇北节度使王承嗣率先竖起反旗,这个与沈璃有着姻亲关系的老牌军阀,调动麾下最精锐的一万五千兵马,其中包含三千重装骑兵。王家的旗帜在北风中猎猎作响,旗面上那狰狞的黑狼图腾仿佛活了过来,对着南方的帝国心脏出无声的咆哮。
紧接着是平卢节度使崔胤,这位以贪婪着称却极善治军的统帅,派出一万二千兵马。值得注意的是,平卢军中有一支两千人的弩手部队,使用的是经过改良的连弩机,能在百步内穿透寻常铁甲。崔胤的响应信写得冠冕堂皇:“清君侧,正朝纲”,但明眼人都知道,他觊觎的是中原的盐铁专卖之利。
范阳、河东、朔方、陇右四镇在随后的三天内相继响应。范阳节度使李光弼出兵九千,其中包含一支一千五百人的陌刀队,这些身披重甲的步兵手持丈余长刀,曾在对蛮族作战中创下“人马俱碎”的骇人战绩。河东镇贡献八千兵马,却包含五百具装骑兵——人马皆披重甲,堪称移动的铁塔。朔方镇九千步骑混编部队以擅长沙漠作战着称,陇右镇八千骑兵则熟悉高原山地地形。
随着沈璃主力南下,沿途景象触目惊心。在沧州,当地豪强郑氏一族全族四百余男丁尽数加入,还带来了囤积多年的粮草三千石。在幽州,三支活跃在边境的走私武装共计两千余人改换旗帜,这些常年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亡命之徒,对地形了如指掌,成为大军最好的前锋探马。
流民的加入更如洪水决堤。三年前黄河决口遗留的灾民、去年大旱逃亡的农民、因朝廷“剿匪”而被毁掉家园的平民……他们扶老携幼,如涓流汇入江河。沈璃军中特设“流民营”,将青壮编入辅兵队伍,老弱妇孺则安置于后勤。不过半月,这些投效者已过四万之数。
“三十万大军”——这个数字在帝国的驿道上飞快传播,每经过一处,就被添油加醋几分。待到消息传至京城,已有版本称“北兵五十万,旌旗蔽日”。
实际情形究竟如何?沈璃麾下真正的战兵约为十二万,其中能称精锐者不过其嫡系五万加六大藩镇挑选出的四万,合计九万。余下三万余为藩镇次等部队。而沿途加入的地方武装和流民青壮约六万,这些部队装备参差,训练不足,多用于后勤、工程和辅助作战。真正的作战核心,仍是那九万经验丰富的边军。
但即便如此,这也是一支足以撼动国本的力量。更可怕的是他们的行军度:从誓师南下至抵达第一个战略要地潼关,一千二百里路,大军只用了十七日,日均行进过七十里。这种度背后,是精密的组织和沿途早已布设好的补给点——这一切显然非朝夕之功,而是经年累月的筹备。
消息传到长安那日,正是谷雨。太极殿早朝的钟声显得格外急促。当兵部尚书用颤抖的声音读出北方急报时,满朝文武竟出现了短暂的死寂,随后才爆出混乱的议论。老丞相王衍手中的笏板落地,出清脆的响声,在这寂静中格外刺耳。
皇帝李暨在御座上沉默良久,他今年才二十二岁,登基不过三年。那张年轻的脸上闪过震惊、愤怒,最终凝固为一种强作的镇定。“众卿,”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中回荡,“有何良策?”
朝堂上的分歧立刻显现。以枢密使为的武将主张立刻调集各道兵马迎击,以中书侍郎为代表的文臣则认为应先遣使招抚,避免战事扩大。双方争论不休时,又有八百里加急送到:沈璃前锋已破潼关外第一道防线,守将战死。
帝国的神经从此绷紧。往北方各镇的使者如离弦之箭般派出,南方税赋的催缴文书雪片般飞往各州,兵器工坊开始日夜赶工,退役的老兵被重新征召……这个曾经强大的帝国,如同被惊醒的巨兽,开始缓慢而笨拙地转身,准备面对来自北方的致命一击。
小主,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,后面更精彩!
在朝廷掌控力较弱的江南、蜀中等地,沈璃起兵的消息激起了不同的涟漪。苏州的丝绸商人开始悄悄转移资产,成都的米商则囤积居奇,等待粮价飞涨。一些地方官员的态度变得暧昧不明,他们既不敢公开响应沈璃,也不愿全力支持朝廷,处在观望之中。
民间谣谚四起。有童谣唱道:“北地狼烟起,朱雀羽翼垂。青龙出水日,白虎踏云归。”术士们暗中解读:北地指沈璃,朱雀象征朝廷,青龙白虎则预示还有两方势力将卷入这场纷争。
茶馆酒肆中,说书人已经开始讲述新的篇章:《沈璃传》《北疆演义》……这些故事将沈璃塑造成受奸臣迫害、被迫起兵的英雄,在民间悄然传播。朝廷虽下令禁止,却难堵悠悠众口。
在这场风暴中,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却是沉默的。河北道的农夫依旧在田里耕作,只是今年的赋税恐怕又要加重;长安城西市的胡商依旧叫卖着香料和珠宝,只是打听消息的人多了;长江上的船夫依旧摆渡往来,只是偶尔会谈起“北方打仗了,盐价要涨”。
他们不懂什么“清君侧”,也不关心谁坐江山。他们只想知道,今年的收成能否吃饱,战争会不会波及家乡,儿子会不会被拉去当兵。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下,是亿万普通人求生存的微小愿望。
沈璃的旗帜在北方原野上飘扬,上面绣着一个巨大的“靖”字——澄清天下,这是他昭告天下的口号。但在每个被迫卷入这场风暴的普通人心中,他们真正渴望的,或许只是一个“安”字。
大军继续南下,距离帝国的核心地带越来越近。而在他们身后,北方的天空下,一个新的时代正在血与火中艰难孕育。这场始于一个人野心的兵变,已经演变成将整个帝国卷入其中的巨大漩涡,它的最终结局,无人能够预料。
实际兵力,沈璃心里有数:能战之兵约十一万,辅兵民夫约四万,总计十五万余。但“三十万”这个数字必须喊出去,它能在心理上震慑敌人,也能吸引更多观望者加入。
大军如黑色洪流般滚滚南下,马蹄踏碎北方的冻土,扬起漫天烟尘。所过州县,守军或开城投降,或稍作抵抗后溃散,或紧闭城门坚守不出。沈璃并不强攻那些无关紧要的小城,他的目标是尽快抵达黄河,渡过天险,直逼京城。
十日后,大军抵达黄河北岸。
时值深冬,黄河部分河段已经结冰,但主流依然奔腾咆哮。对岸,朝廷的防线已经构筑完毕。慕容玦紧急调集的各地驻军陆续抵达:西平王慕容恪率三万勤王军从西线赶来,河北道节度使领两万兵马守备渡口,河南道节度使集结三万大军沿南岸布防,加上从各地抽调的地方驻军,朝廷在黄河一线聚集了约十二万兵力。
双方隔河相望,战云密布。
沈璃站在北岸一处高坡上,用千里镜观察对岸敌情。黄河宽阔如带,在冬日灰蒙蒙的天空下泛着土黄色的波光。对岸旌旗招展,营寨连绵,隐约可见士兵移动的身影和战马的轮廓。
“将军,探子回报,”韩青策马上坡,脸上带着长途奔波的疲惫,“对岸主帅是西平王慕容恪,副帅为河北道节度使刘裕。朝廷军分三段布防:上游孟津渡由刘裕亲自镇守,中游白马渡由慕容恪坐镇,下游官渡由河南道节度使防守。各渡口均筑有防御工事,河面船只已被全部收缴或焚毁。”
沈璃放下千里镜,眉头微皱:“慕容恪他居然亲自来了。”
西平王慕容恪,皇帝的堂叔,年过五十,是宗室中少有的知兵之人。年轻时曾随军征战,虽无显赫战功,但用兵稳健,深得先帝赏识。更重要的是,此人性格刚直,对朝廷忠心耿耿,是块难啃的骨头。
“将军与西平王有旧?”孙文在一旁问道。
“听说过。”沈璃回忆道,“那时他还是郡王,奉命巡视北疆。为人正直,治军严谨,但对部下颇为宽厚。有一次他手下违令出击,虽取得小胜,回营后却被他杖责二十。他说‘军令如山,今日你违令得胜,他日他人效仿违令败北,该当如何?’”沈璃没有说,那个手下就是自己的亲哥。
韩青道:“如此说来,是个难对付的角色。”
“难对付,但不是不能对付。”沈璃眼中闪过锐光,“慕容恪用兵求稳,不善奇袭。他必会采取守势,等我军渡河时半渡而击。所以,我们不能按他的节奏走。”
他转身走下高坡,众将紧随其后。回到中军大帐,沈璃指着悬挂的黄河地形图:“黄河千里,他防得住几个渡口?传令下去,全军分三路:韩青率两万兵马,大张旗鼓准备渡河器材,做出要从白马渡强攻的态势;孙文率一万精兵,秘密向上游移动,寻找可渡河之处;我自率主力,向下游迂回。”
“将军是要声东击西?”孙文眼睛一亮。
“不止。”沈璃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,“我要让他顾此失彼。慕容恪兵力虽与我军相当,但分守三处,每处不过四万。我集中主力攻其一点,便有兵力优势。而他要调动其他渡口守军支援,就需要时间。这段时间差,就是我们的机会。”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“但若他识破计策,集中兵力应对呢?”韩青问。
“那就看谁更快。”沈璃沉声道,“黄河结冰情况如何?”
“探子回报,上游山区河段冰层较厚,可通行人马。中下游因水流较急,只有岸边有薄冰,无法承重。”韩青答道。
沈璃点头:“孙文,你这一路任务最重。我要你五日内找到可渡河之处,并搭建浮桥。能做到吗?”
孙文肃然抱拳:“属下定不辱命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