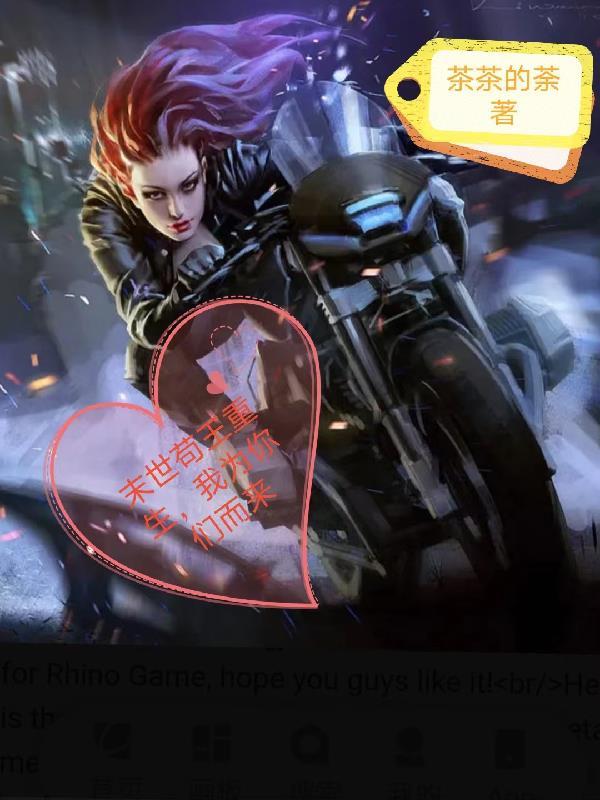大文学>和脱衣舞女郎妈妈一起穿越到异世界 > 第17章 公孙大人居然是半个阳痿(第13页)
第17章 公孙大人居然是半个阳痿(第13页)
那长袍裹得再紧,也裹不住那腿——那腿长长的,直直的,在那袍子下面若隐若现的线条。
她站在那儿。
站在那橙红色的光里。
站在我面前。
像一座山。
像一尊神。
像我的女人。
我伸出手。
把她揽进怀里。
她靠在我胸前。
那身子软软的,热热的,带着那晚香玉的残香,带着那汗味,带着那东西的腥味——可那味道混在一起,是她的味道,是我闻了几十年的味道。
我把脸埋在她头里。
那头高高的,盘着,插着那根绿松石的簪子。那簪子在那光里绿绿的,亮亮的,像一滴水。
我闻着她。
抱着她。
抱着我的妈,我的女人,我的妻。
她的手环着我的腰。
那手白白的,软软的,在我腰后交握着。
她开口。
那声音闷闷的,从她埋在我胸前的嘴里出来。
“儿啊——”
“嗯?”
“我们回去吧。”
“好。”
我们松开。
手牵着手。
继续走。
走在那黄昏的风里。
走在那橙红色的光里。
走回我们的营帐。
那营帐就在前面,不远了。那白色的帐篷在那光里泛着光,像一堆雪。
我们走进去。
走进那帐篷里。
那帐篷里还是那样——那厚厚的皮毛铺在地上,那小小的炉子还在燃着,那火光一闪一闪的,照得满帐都是暖暖的红光。
她松开我的手。
走到那案子旁边。
把那两样东西放在案子上——那封册封文书,那本贸易许可书。
然后她转过身。
望着我。
那眼睛亮亮的。
那亮里有笑。
她抬起手。
开始解那藏青色长袍的带子。
那动作很慢。
慢得像那年出租屋里她第一次给我跳那种舞的时候——那种慢。
那带子解开了。
那长袍散开。
从她肩上滑下来。
滑下来。
滑到地上。